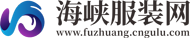文艺论坛丨张灵:后现代的精致和落寞
后现代的精致和落寞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夏商小说的审美解读
文/张灵
摘 要:夏商小说特别是其一部分中短篇小说,从美学角度而言,追求着一种气韵流荡、晶莹疏朗的空灵之美。作品常常不对与情节有关的生活内容坐实描述,一些细节被省略、悬置了,变成了艺术的留白。时间的跨度、人事的变幻、人物行踪的不定,同样透出一种空灵意味。不过,夏商这些小说大多呈现了生活的复杂、暗淡甚至卑污、恶劣的方面,映射了商业时代的都市年轻一代生活的形式化、符号化以及他们内心世界的种种症候,也表现了夏商对人性、人生、社会问题的反省、批判和对个体生命的悲悯与关怀。这些小说的空灵和古典美学的空灵有着不同的滋味,呈现出某种精致而落寞色彩,让人联想到暮色中玻璃钢主导的、摩天大楼林立的城市景象。
关键词:夏商小说;小说美学;生活的形式化;都市生存景观;生活的流动性
夏商小说,特别是他的中短篇小说在美学上有很多特点,比如在叙述上具有浓厚的先锋色彩,往往打断了生活或故事原有的秩序而重新按照自己的某种艺术旨趣作出处理,同时他的小说常常追求一种戏剧性,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小说的整体布局和故事情节的安排,而在更具体的表达层次,他的小说则表现出对修辞的注重,隐喻、比喻、伪陈述、象征等,都有广泛的运用;从美学角度而言,他的一部分中短篇小说追求一种气韵流荡、晶莹疏朗的空灵之美。
一
《口香糖》(2000)是一篇戏剧性很强的短篇小说,它给了三两个场景,演示了几幕人生的片段,对人们的婚姻爱情生活的真实情景作了巧妙的呈现。作品选择的主要舞台是一间都市的酒吧。 “入夜时分,吧台后面的亚诺擦着一只玻璃高脚杯。没有点滴的灰尘,也不能有细微手印。亚诺的脸孔和玻璃杯一样冰冷,散发出如同刀锋的寒光。”这完全是一个电影的近镜头。我们知道,现代都市酒吧往往就是一个极其光鲜现代的场所,这种场所往往窗明几净、装修讲究,又因为摆设着酒瓶、酒杯等各种酒器,就更显空灵。作者所刻画的“玻璃杯一样的冰冷”“刀锋的寒光”更增加了这种空灵感的现代色彩。而亚诺这个调酒师的动作也透出简洁和精确的色彩,散发出科学所隐含的精密、透亮、唯一,换句话说,没有拖泥带水、没有粗糙和简陋,这自然与空灵之美有着曲折的相通。“能够解释他孤寂心态的,除了缓慢而精致的手势之外,是左腮那块不停嚼动的咬肌,和淡而无味的口香糖。”孤寂的心态、重复的嚼动与“淡而无味的口香糖”一致,显示着人物内心的空无,只是给这个空灵的环境增加了现代乃至后现代的消极色彩和落寞情味。“他离开吧台,来到大堂,推开若干扇门中的一扇”,这个现代性的场所虽然被一扇扇门隔成了多个狭小一些的场域,但一扇扇的门,又意味着敞开与连同,乃至空透。在一个小空闲,罗雪芝在亚诺的柜台后的小房间无意中发现,那里有一个窥视镜头,可以让亚诺看到各个包间里的情景,这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酒吧的透明感。
场合方面的空灵不用细数。更重要的是故事,罗雪芝来上班,这是第一天,这是一份在特殊场合的特殊的工作,于是他的丈夫、现在一家水站送水的下了岗的前工厂小干部也随后而来坐在了酒吧的一角,罗雪芝像对一个陌生客人那样走到他的面前,他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并不花钱消费,她虽然觉得丢人但也懂得他的心思。这是第一天的场景。另一个场景在新加坡华人、罗雪芝从前的闺蜜和同学许明洁的房间,许明洁是这家酒吧的老板,她打算叫罗雪芝随后帮她经理。她也说了从前没有说起的秘密,许明洁当年更早和罗雪芝的丈夫相处,后来他转向了罗雪芝,而许明洁则认识了一位新加坡人,他的财富打动了她。在最后一个场景又回到了上一天的酒吧,场景几乎一样,只是罗雪芝的丈夫比前一天多了一分老练,他要了一杯免费的柠檬水。更重要的一笔是,一会儿进来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他把亚诺叫到一旁小声带比画地说了一通,看得出来是有关于罗雪芝的。完了这男人转身走了,一会儿之后,罗雪芝的丈夫也不知何时消失。而亚诺一边像刚才那样擦着杯子、嚼着口香糖的同时,不时投向罗雪芝的短暂一瞥里多出了某种特殊的意味。这就是小说交代的基本内容,留下了很多的空白点: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是谁?他和亚诺交涉了什么?他是罗雪芝的丈夫请来的吗?是来警告亚诺别在罗雪芝的身上打什么算盘吗?
作者没有坐实这些与情节有关的内容,作者的叙述安排有时将一部分社会生活现象的描写归于“无迹”, 即把一些细节省略了、悬置了,生成了一种艺术的留白,这样就规避了对生活现象的满篇式的具体实在的刻画的局限,而使作品在内容上形成“有无”相生、相映的艺术效果,于是作品变得更加耐人寻味,也增加了空灵之感。{1}
与《口香糖》有某种亲缘性的是《水果布丁》(1997),它们在场景上有相似点,后者的故事有两场戏。一个在办公室:华秋姬坐在一家广告公司人力部经理韩回的办公室应聘。一个在咖啡屋:韩回的同学鲁家风和他的妻子要“顺路”来找韩回在附近的咖啡馆见面,韩回顺便邀请华秋姬一起去咖啡屋。两个场景里的短暂两幕呈现了职场生活的一隅,对华秋姬这样马上走向社会的年轻人而言,生活充满了不可捉摸的变数。也许她会是幸运的,但未来生活的周围无疑也潜藏着各种令人会感到不堪入目的人事景象,就像小说场景描述中暗示的那样。如果说她前来招聘单位面试是一个约定的行为的话,招聘主导者对她的初见印象则是出人意料的,而更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是她被邀请与人力经理同去咖啡屋应酬、与没有事先约定的朋友会面。他们的职场经营成败是风云变化的,人物之间的交往也是充满了随意和偶然,小说没有中心事件和中心主题,只是呈现了生活的瞬息万变和动荡不定,在流动中作品通过两个场景捕捉、描绘了现代都市流动变幻的生存景观的生动一幕。那个水果布丁不仅是弹性的、细嫩的乃至有一种透明感,而且它的有无也是可以即时变化的。小说像是没有主题,这与走进咖啡屋的另一位女士的香水一样缥缈。
二
把生活的流动性彰显得更加鲜明的是《金色镶边的大波斯菊》(1999),它讲了两个朋友分手前一段短暂的送别行程里发生的事情:谢文和江术拼车过江邂逅夜总会领班吉娜,又通过捡到的受伤鸽子嘴里的一张小纸棍联系上薇薇,在夜总会又认识了莉莉,谢文在床上看到薇薇背上的文身下面实际是一条刀疤,薇薇含泪离去,江术又让莉莉去陪谢文,谢文拒绝后三人决定找个饭馆吃饭聊天,这时接到成都的朋友方小方打过电话来说自己得了癌,希望江术和谢文再去成都相见,还开了几句玩笑,三人相聊甚欢。挂断电话不久,江术的手机又响了起来,方小方女友说方小方从十六楼跳下去了。江术和谢文在街头抱头哭了起来。情节的叙述一如他们短暂的相聚,行云流水又涟漪回环牵连,在峰回路转的场景变化中不经意地扯出几个萍水相逢的特殊女性和她们光鲜麻木似的生活背后的人生故事与内心伤痛,方小方的电话来得自然随意,但进一步给作品增加了沉痛的一笔,莉莉与前男友的一笔虽没有展开,但对故事的丰富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萍水相逢的不仅是人物,更是他们每个人的命运,我们醒悟到那些在城市街头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的人流不再是随风飘零的枯叶,而是游走的行吟者,他们或在讲述一则不朽的寓言,或在编织一则瑰丽的传说”,{2}但也许只是在没有观众地扮演一场黯淡的哑剧。这篇小说里的生活就是这样,种种的历险组成的并不封闭的连环,流动和偶然性让故事摇曳多姿,叙述间流荡着某种料峭的气息,让人觉得字里行间寥落舒朗,毫无凝滞闭塞之感,而有一种叙事的空灵,而叙事的空灵更衬托出生活的沉重、郁闷乃至无路的荒凉与空无。
《刹那记》(1998)的标题就暗示了对瞬息万变的世界的某种禅性的凝目。张雷和蓝帕尔曾是劳动局第三技校的同学、好朋友,而且住在同一幢楼。技校二年级的夏天,他们横穿马路去追赶两个漂亮女生,在决定命运的一瞬间发生了一起车祸:张雷差点被一辆汽车撞倒,蓝帕尔去拉,却被反向的另一辆车撞翻在地,从此失去了一条腿。蓝帕尔后来开了一家杂货店,但婚事成了难题,好友张雷夫妇为他介绍一位合适的姑娘,在餐桌旁,他发现这姑娘也跛着一条腿,他当即拒绝了这姑娘,其实是拒绝自己的命运。两个男孩在阳光灿烂的夏天追赶两位漂亮的女生,这是快乐的事情,可以定格到记忆成为一个永恒的画面,但天有不测风云,瞬息之间两个男孩的命运出现了诡谲的情形和出人意料的转换,张雷有惊无险,蓝帕尔却因好心的一个举动而蒙受灾难,最终和好友的人生形成难以接受的对比。刹那时间中的变幻与前后一定跨度的生活变化、人我对比,特别是相亲见面之际蓝帕尔对另一方跛足的突如其来的发现和同时受到的心理冲击与作出的命运抉择,都使小说具有了某种类似佛境的空悲之感,小说关键时刻的瞬息万变和前后对比,则给人流荡变幻的空灵气息。
《集体婚礼》(1998)也渗透出一种对人世与人生的空明悲凉之意。季有城和蒋怡琴参加一场百对新人的集体婚礼,中途季有诚发现一个盘着堡式发髻的新娘是大学同学荆一丁的前女友,这姑娘也认出了季有城,带出一段往事:毕业那年夏天,荆一丁曾把这个当年做餐馆服务员的姑娘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并得到了她,不过随后又甩了人家,不久荆一丁就被一辆饭盒车撞倒在地死亡。占有一个满怀期待的姑娘又将人家甩脱,的确是一个让人哑巴吃黄连的不道德的轻率行为,甚至是一个巨大的罪过,但因此吃亏的姑娘就将另一个年轻的生命置之死地也是一种更大的残忍。罪过是双重的,生命的恍惚和无常与佛家的空悲之念声气相通,在一个盛大欢乐的集体婚礼上,季有诚却因偶遇而再次想起、看到别人的依稀苍凉的人生,也同样是欣悲交集。时间的跨度、人事的变幻不定,同样透出一种空灵意味。
《金陵客》(1998)也是在运动中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时尚杂志广告部经理金陵客从南京来到上海,偶遇留日归来的儿时邻居张云,傍晚宴请一些老朋友吃饭,张云没有赴约,而是约他单独见面。饭局结束后金陵客又约“我”和“我”的模特女伴秀拉去张云所在宾馆的旋转餐厅再聚,赶到宾馆再次巧遇刚才在咖啡店遇到的故人帅孟棋和他的日本女友宫泽惠子。凑巧的是帅孟棋与张云在日本时也认识,宫泽惠子不仅婉拒了金陵客共聚旋转餐厅的邀请而且显得脸色不好。到了旋转餐厅,金陵客却借故把“我”招到洗手间说话,其实他是在“赌”,如果“我”来了,他马上就离开这里去车站,如果“我”不来他就留下来和张云作伴,他的顾虑是很多女人在日本并不仅仅是靠通常的工作立身,他担心会不会因为露水姻缘而染上难以启齿的暗疾。说罢,金陵客大踏步走向电梯,为了阻止他这种不负责任的退场,“我”跟进了电梯,在电梯中途停靠时,又遇见帅孟棋沮丧地走进来,他的领口还有点破损,冲着“我们”苦笑了一下,电梯到了底层他就匆匆告辞而去。“我”很懊恼地回到餐厅,恶作剧地把张云叫到一边对她说,金陵客担心自己的梅毒伤害到她就不辞而别了。现在就剩“我”和秀拉了,“我”把她的手握住。但“我”和秀拉彼此心照不宣,我们不会选择对方结婚。这样的情节,如同一阵小旋风在上海的几个街区几个场所迅速刮过。风流云散般的不断转移和变化迅速的轻快节奏有一种轻逸之感,与那些场所的精致剔透的风格极为和谐、男女主人们之间缱绻缭绕与萍水相逢、率尔掷情的作风让字里行间洋溢着后现代的风情景致。这段故事有点像过去年代的儿童们爱玩的翻绞游戏,橡皮筋在两个玩伴的四只手指间迅速变换位置和结构,看似复杂,实又简单,简单的玩具上的错综变化就带给人眼花缭乱般的快感。流动和变化的生活与光鲜现代的环境、时尚的衣着、精心的化妆交相辉映出一种现代气息,有着某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晶莹、轻巧、灵妙。
三
不过,夏商这些小说所呈现的空灵,和传统的古典意味的空灵并不完全相同,它们有着不同的滋味。孙犁先生评价莫言小说《民间音乐》时所说“空灵”正取这样的意涵:“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说的气氛还是不同一般的,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3}因此可以说,高妙的手法、风雅的内容、旷达的胸怀构成了古典空灵美学的重要成分。而夏商小说作为一种现代叙事文体的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已经远离了古典空灵的典型领域山水田园、宫苑闺阁和个人高蹈情怀抒发的方面,作为当下时代的小说作品,夏商小说更主要的是在叙事艺术的虚实、疏密、正侧、迟捷等方面表现出空灵美学的意趣,而它们表现的思想内容,更多是对现实的反映,呈现出人性、人生和生命以及社会的复杂、暗淡甚至卑污、恶劣的存在,表现出对人性、人生、社会问题的反省、批判和对个体生命的悲悯与关怀。
《一人分饰两角》(1997)以旁敲侧击的叙述手法巧妙展示了社会底层的某些景象。职业保险推销员桑蚕遭到了两个歹徒的抢劫,歹徒划伤了他的额头还抢走了他的手表。当他的女友常羽进来看见桑蚕额头贴着纱布才知道了他遭到抢劫的事情。他也不打算再做辛苦又冒险的保险推销了,还邀请她一起开家书店。但是桑蚕不知道常羽还有另一个名字——雪莉。葛娜在给雪莉打电话,刘保和成卫东在等她。葛娜无意中看见刘保的袖口有血迹,她惊叫起来,成卫东连忙说那是吃肯德基掉的番茄酱。没有等来雪莉却先等来了尤丝露,她给自己的胸部垫了很高的海绵,她想跟雪莉争抢那个喜欢丰满、出手大方的日本人。葛娜悄悄告诉了尤丝露看见血的事情和刘保手上的浪琴表。她说,这两个东西要死了。葛娜使了个眼色,三个姑娘扭身走到了外面,见到一辆出租车准备上车,刘保、成卫东追了出来,他们凶相毕露,葛娜和雪莉反应快、钻进了出租,尤丝露却留在了外面,出租车急忙开动了。这个小说也是截取了城市生活的一小会时间里的流动性情景,却折射出为数不少的一批年轻人的生存状况、谋生方式和他们不同的品行操守。雪莉、常羽两个名字一个人,分饰两个角色,一个是“清纯少女”的定位与认同,一个是风尘女子的身份与承受。从小说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葛娜、尤丝露和雪莉一样虽然为了生存在城市里干着不为法律、公序良俗接受、认可与尊重的营生,但她们的心地有基本的善良和分寸,使她们不会干伤天害理的事情,而刘保和成卫东可能是她们的牵线人兼保镖,但他们与那几位女性相比一般来说谋生的手段要少一些,因而不免兼干着铤而走险的勾当。小说没有正面描述成卫东和刘保抢劫手表的过程,却通过人物的关联把抢劫的事件与桑蚕和成卫东、刘保以及几位女性的人生关联起来,当然最关键的是把常羽和雪莉分饰的两个角色连接了起来,同时也是把刘保、成卫东和雪莉们合作的生活与他们背着她们另行从事的勾当关联起来。成卫东们的抢劫和雪莉们可能从事的色情营生都不是作者所要正面展开的社会生活内容,如同标题所示,小说的用意就在对雪莉(常羽)“一人分饰两角”的特殊人生处境的展示。这才是小说的真正关切所在。显然这是在呈现一个问题、记录一种问题的人生或社会现象,因此《一人分饰两角》在艺术手法上虽然多有空灵之妙,但它的内容和旨趣在于对生活中的灰暗、阴郁、沉重层面的反映。常羽一人分饰两角,对比之中也可见出她的迫不得已、一定的自我放弃和对纯真美好人生的内心认同与向往。这种生活与精神心理状况可能也不仅是她的,而是葛娜、尤丝露们所共有的,区别只在于每个人内心的纠结、冲突和不安的程度有所区别。因此这样的小说,正是一种“问题小说”,它们不是像传统的空灵作品那样令人感到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得到精神的陶冶,它们首先是对社会作反思和批判的。
《猜拳游戏》(1997)对人性和人的命运的无定和无常作了精妙的演示。“夏商”和药剂师萧客及其妻子丛蓉约好在傍晚共聚晚餐,先等到的却是丛蓉,原来萧客出门前被警察截走了,原因是一只“鸡”供出了萧客,她的包里有萧客的名片。小房间里连萧客陆续关进了七个人:文学编辑宋、电厂秘书张、炒货业务员王、讲师葛、采购员唐、船老大于。大家都一脸沮丧,唯一的例外是讲师葛,那张脸居然幸灾乐祸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两个人暗地里的交易,她死咬住你,你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七个人纷纷质疑有谁真和那“鸡”发生过关系而让大家跟着受牵连。有人在开始观察谁是真正的嫖客。秘书张提议大家做猜拳游戏:最后一个出局者将被假设为那个真正的嫖客。结果船老大于最后出局,然而,他却是被最早释放的人。“猜拳游戏”的结果都和实际被先放的人不一致。第三天下午,萧客被释放,找“夏商”打听丛蓉的消息,“夏商”没有告知丛蓉正和幼儿园同事傅建玲住在一起,她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这个“猜拳游戏”像一切游戏一样都只有一个空洞的形式,并没有实质的意义。七个嫌疑人并不能决出谁是真正的“祸根”,实际的命运总是出乎意料,难以把握,如同“夏商”和丛蓉当年的恋爱关系以及丛蓉和萧客的婚姻关系。“夏商”原本和丛蓉是一对恋人,萧客同时也在追求丛蓉,于是两人因误会分开,萧客和丛蓉成为夫妻。当然在这种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人生感之外,小说也透露出了人性的瞬息万变的可能,更透出了对爱情婚姻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信任的无力抉择之感。作品对人的婚姻心性之缘充满了悲观和虚无的情绪,而人的互认与互守之不可把握的无常绝望之感恰是“猜拳游戏”这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形式游戏中沉甸甸的东西,它弥漫在作品描绘的摇曳、空洞、流动的浮世景象间{4},在空灵的叙事格调里散发着晶亮、冷冰的色彩。
夏商这些小说无论沾染或含有那种因素构成的空灵,其实都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古典美学的超拔、高雅的空灵有着不一样的色彩,它们固然是小说家的灵性的表现,显示了作家在形式上的精巧智慧,使小说的叙述不再笨重、拙实,同时,这些小说也放弃了指义途径的思想灌输,把对生活的反映和理解变成了托马斯·艾略特所谓的非个人的,并借“客观关联物”而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赋予作品形式{5},或使情感凝注转化为形式。其实这种空灵还可以从更深的意趣与根源上进一步挖掘,学者李幼蒸在评述罗兰·巴特的“文本享乐主义”主张的时候说道:“‘娱乐’或‘快乐’成为一种空灵的能指,成为无目的的目的;其所谓快乐实际上是内心极度颓丧的一种映像。”{6}而这一阐释从夏商小说描写的内容来说,也正映射了商业时代的都市年青一代生活的形式化、符号化和他们内心世界的某种症候。因此,夏商这些小说的空灵是一种现代的空灵,不再散发古典的雅致,而是呈现为一种后现代的精致和落寞,让人联想到暮色中玻璃钢主导的摩天大楼林立的城市。
注释:
{1}简圣宇:《中国传统意象理论发展历程刍议》,《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2}王陌尘:《〈标本师〉:一则解剖人性冰山的寓言》,《文艺报》2017年5月17日。
{3}孙犁:《读小说札记》,《天津日报》1984年5月18日。
{4}肖涛:《夏商:用文字勾勒流动的浮世绘》,《文艺报》2018年10月31日。
{5}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8页。
{6}李幼蒸:《译者前言》,摘自罗兰·巴特著,李幼蒸译:《写作的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法治建构的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BZW18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外事职业大学综合学院)
X 关闭
推荐内容
- 北京国际电影节发布主宣片 李雪健宋佳齐溪黄轩联袂打造短片
- 全国多地复工复产加快 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和设备利用率指数亦表现良好
- 中央网信办:建立负面清单 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管理
- 协同发力 内蒙古超额完成煤炭外运保供任务
- 空间科学家倡议:推进空间技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
-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多地出实招为企业减负
- 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有望实现 新动能待进一步挖掘
- 31省份乡村性别比数据公布:全部男多女少
- “四叶草”邂逅“迎客松”:外企追赶中国机遇
- 清华大学:全面审查文科博士学位论文质量
最近更新
-

文艺论坛丨张灵:后现代的精致和落寞
焦点 -

原神明星聚画第五关攻略
焦点 -

(长江云)咸宁咸安:95后女孩回咸创业,她说终于找到了开店的意义-世界热点
焦点 -

湖南省2023年高级经济师考试报名入口已开通
焦点 -

每日热讯!色情平台封锁美犹他州网民IP,AV女星拍视频揭真相
焦点 -

【全球独家】四大证券报精华摘要:5月4日
焦点 -

报道:坚持不懈的意思解释_坚持不懈的意思
焦点 -

当前热门:返程高峰来袭!石家庄发布出行提示:这两个时段拥堵缓行压力最大
焦点 -

你的爱就像火苗把我的心燃烧_你的爱就像火苗
焦点 -

煎鸡脯肉的家常做法_鸡脯肉的家常做法
焦点 -

环球热头条丨樱舞少女的圆舞曲有妹线吗_樱舞少女的轮舞曲手游好玩吗 樱舞少女的轮舞曲手游玩法简介
焦点 -

当前资讯![擅长捉弄的高木同学]考试结束与接送
焦点 -

扬新风聚人气汇民心 海口秀英区举办2023年荔枝月首届排球邀请赛[图]
焦点 -

环球通讯!节前一周 机构“盯”上了眼科医院
焦点 -

【环球热闻】女主温柔恬静的小说_女主温柔恬静的宠文
焦点 -

匕首是什么意思_匕首指的是什么|全球快播
焦点 -

飞阅万宁大花角 打卡这片鹅卵石镶嵌的玻璃海湾 全球快讯
焦点 -

液压油消泡剂分享:让你不再挣扎如何灭泡 世界今日讯
焦点 -

戏曲大咖齐聚泉州 探讨南戏与古老剧种传承之路-每日消息
焦点 -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在中国有用吗?
焦点 -

特斯拉在美国恢复销售Model 3长续航版,价格降了1万多美元
焦点 -

世界微资讯!涿鹿县南山区获评“国家级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区”
焦点 -

女龙男兔结婚是大忌 女龙男兔婚姻缘由
焦点 -

夯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数字底座”_全球速看料
焦点 -

猎豹移动公司美股跌10.61% 热推荐
焦点 -

宁夏印发意见全面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世界聚看点
焦点 -

NBA近43年首次中锋包揽连续3年MVP 全球报道
焦点 -

37岁魏晨官宣当爸,老婆于玮孕肚照曝光,宝宝性别未公布
焦点 -

当前速递!“火焰蓝”深入热门景区守护游客安全
焦点 -

全新涂装,配置升级,极狐阿尔法S和阿尔法T森林版亮相-世界热资讯
焦点 -

不愁卖了?特斯拉Model 3/Model Y官宣涨价2000元
焦点 -

甘南房改房继承纠纷律师收费要多少
焦点 -

用什么可以去眼袋_用什么去眼袋效果好 环球微速讯
焦点 -

环球热头条丨故事里来的小木偶
焦点 -

假期在岗位 | 练就“绝活儿” 穿越困难振翼飞翔
焦点 -

小米9手机怎么样值得买_小米9手机怎么样_通讯
焦点 -

热点聚焦:摩氏硬度计的十种矿物_摩氏硬度
焦点 -

数字黑洞123 数字黑洞-天天播资讯
焦点 -

沙尘暴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导致汽车追尾 至少6人死亡
焦点 -

中超第10轮广东德比 恒大2-0击败深圳佳兆业
焦点 -

近百位美食店主齐聚,这群普陀人共商“舌尖上的安全”→|焦点日报
焦点 -

助力国产汽车“走出去” 中欧班列(成都—莫斯科)成功首发
焦点 -

天天即时:国际最新研发一种非侵入性语言解码器 可经脑扫描识别语言
焦点 -

每日速读!繁花盛放 2023上海月季展迎接八方来客
焦点 -

聚焦:问宿命是否再多久再持久再永久是什么歌
焦点 -

新动态:美国伊利诺伊州州际公路连环车祸造成至少6人死亡
焦点 -

热头条丨绥中县气象局发布大风蓝色预警【Ⅳ级/一般】【2023-05-02】
焦点 -

神了!一天挖出上百块籽料,他是如何做到的?
焦点 -

qq游戏里的头像怎么改_我想重新换一下QQ游戏里的头像 怎样上传图片|速递
焦点 -

新京报网_关于新京报网简介
焦点 -

长期戴眼镜会变金鱼眼?未见得
焦点 -

河北围场三力合一打造马铃薯产业化强县
焦点 -

今日聚焦!督察组现场检查:汕头小公园、广场轮渡等处有流动摊贩!
焦点 -

“五一”假期我在岗丨长沙高铁西站施工正酣
焦点 -

蔚来4月交付量为6658辆 同比增长31.2%-当前要闻
焦点 -

清炒虾仁的传统做法窍门_清炒虾仁的正宗做法
焦点 -

世界微速讯:韩国在野党成员登上独岛:谴责政府“屈辱外交” 呼吁日方就历史问题道歉
焦点 -

花溪十字街,让文创成为旅游业态新地标 每日短讯
焦点 -

2023上海车展:劳斯莱斯新款幻影高定版亮相
焦点 -

2023上海车展:i7 M70L体验 1100牛米还带M的宝马电动车_全球新消息
焦点 -

播报:pt950铂金回收价格今日多少钱一克(2023年05月01日)
焦点 -

当前观点:暂停售票!西安一景区通告:临时限流!
焦点 -

遇见福建:“五一”去宁德邂逅“诗与远方”|焦点资讯
焦点 -

长三角铁路5月1日预计发送旅客超340万人次
焦点 -

天天资讯:2023攀枝花中考分数线预测 多少分上高中
焦点 -

游客在三亚遭遇“铁皮石斛刺客”,二两多被要价2100元,多部门介入处理
焦点 -

【速看料】宋谋方
焦点 -

博物馆美术馆成中国民众“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 热闻
焦点 -

lol输入不支持并黑屏_lol输入不支持_每日动态
焦点 -

每日热点:半场:拜仁0-0赫塔,马内错失良机,科曼禁区倒地未获点球
焦点 -

专注人体工学 Fizik推出全新Aliante座垫 焦点资讯
焦点 -

热议: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侗乡传统村落精品旅游环线旅游攻略
焦点 -

散步莫怀戚原文解析_散步莫怀戚原文
焦点 -

绝对权力电视剧下载迅雷下载_绝对权力txt下载
焦点 -

美国伊利诺伊州法官暂停攻击性武器禁令 世界短讯
焦点 -

天天实时:这个五一,常德“火”上央视!
焦点 -

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1966万人次 创历史新高|环球今亮点
焦点 -

苏大维格:公司研发的衍射光波导镜片和投影屏等是AR/VR及AR-HUD的核心硬件
焦点 -

全球新动态:北京铁路4月29日进出京超141万人次 较去年增1484%
焦点 -

方特旅游app官方下载_芜湖方特水上乐园_天天微资讯
焦点 -

快讯:原创手绘 | 必读!假期风险防范提示卡
焦点 -

市热线办制定服务保障应急处置预案-观察
焦点 -

无障碍卫生间图片_无障碍卫生间|世界即时看
焦点 -

全球短讯!现代诗歌大全100首励志青春(小学生现代诗歌大全短的)
焦点 -

现代诗歌理论_关于现代诗歌理论介绍_世界新要闻
焦点 -

8000亿军火巨头拿下540亿大单
焦点 -

术前唱歌鼓劲 术后鲜花慰问 手术室里 九旬老战士享受“特殊”待遇
焦点 -

比亚迪秦EV,售价15.58万,纯电续航405km,零百加速15s
焦点 -

国家级女子帆船赛即将落地河南三门峡
焦点 -

括号的用法及举例-全球视讯
焦点 -

【焦点热闻】市医疗保障局举办全市医保基金监管业务培训会
焦点 -

天天观热点:哈姆更衣室激情演讲:今天的防守表现是我们未来比赛的标杆
焦点 -

知情人士:第一共和银行或于本周末被接管并出售 新消息
焦点 -

当前观点:周末祝福短信大全_周末祝福短信有哪些
焦点 -

世界通讯!kubectl命令使用(四)
焦点 -

拭目以待!平行论坛特色亮点第四弹剧透来了 环球新资讯
焦点 -

鬼灭之刃第三季锻刀村篇樱花动漫_元气少女缘结神第三季
焦点 -

买回来的仙客来怎么种植 买回来的仙客来如何种植 头条焦点
焦点 -

建筑工程师证书查询_建筑工程师证
焦点 -

告别五福一安!iPhone 15支持27W快充 环球速讯
焦点
Copyright © 2015-2022 海峡服装网版权所有 备案号:皖ICP备2022009963号-10 联系邮箱:396 029 142 @qq.com